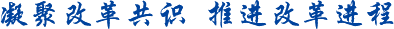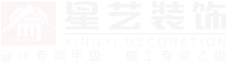43歲的法國(guó)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托馬斯·皮凱蒂(Thomas Piketty)一直對(duì)回到19世紀(jì)歐洲的貧富差距狀況抱有警惕��。很顯然���,在他看來(lái)�,10%左右的人口掌握國(guó)家90%的財(cái)富���,這不僅有悖于公平�����,更無(wú)異于給國(guó)家的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戴上了沉重的鐐銬�����。但讓人擔(dān)憂(yōu)的是�,皮凱蒂發(fā)現(xiàn)����,我們今天距離19世紀(jì)的歐洲不平等狀況,恐怕不是走得更遠(yuǎn)��,而是更近了�。
人類(lèi)對(duì)貧富差距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世界文明史的源頭,甚至可能早于貨幣的誕生���,把時(shí)間軸拉近到19世紀(jì)�,在諸如巴爾扎克等著名作家的文學(xué)作品里�,貧富差距和社會(huì)階層的不平等也貫穿著一個(gè)時(shí)代書(shū)寫(xiě)的主題��。無(wú)論是文字還是數(shù)據(jù)�����,影像還是公式�,過(guò)度分化的社會(huì)階層與不平等現(xiàn)象都自有其表述���,然而對(duì)于貧富差距是否超出了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的忍耐限度���,每個(gè)人都將只能依靠已知的歷史和經(jīng)驗(yàn)作答����。
皮凱蒂?zèng)]有在他的著作《21世紀(jì)資本論》中就這個(gè)“限度”給出任何明確的標(biāo)尺,正如上帝從不擲骰子��,在缺乏足夠的數(shù)據(jù)支持�����,以及影響因素眾多的情況下����,對(duì)未來(lái)做出判斷往往是不明智的��。誠(chéng)然���,“歷史會(huì)怎樣演變?nèi)Q于社會(huì)如何看待不平等,以及采取怎樣的政策和制度去衡量與改變不平等�����。”從這個(gè)意義上來(lái)說(shuō)��,皮凱蒂無(wú)疑是樂(lè)觀的����,即使這棵大樹(shù)上布滿(mǎn)蟲(chóng)窟,但他仍然相信可以通過(guò)一系列的公共基礎(chǔ)設(shè)施與稅收制度讓不平等性的惡化早日懸崖勒馬���。
雖然皮凱蒂的身份是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者�����,但他更愿意將自己當(dāng)做一名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家�。他不無(wú)遺憾地發(fā)現(xiàn)�,自20世紀(jì)70年代起,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已經(jīng)對(duì)財(cái)富分配和社會(huì)階級(jí)問(wèn)題喪失了絕大部分興趣。因此他試圖通過(guò)這本書(shū)�,重新將分配問(wèn)題納入到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的核心。“這應(yīng)該是最核心的問(wèn)題��,我們長(zhǎng)遠(yuǎn)怎樣發(fā)展��,我們沒(méi)有任何理由認(rèn)為增長(zhǎng)時(shí)每個(gè)群體分配得到的收益比例應(yīng)該固化���。”而對(duì)作為新興國(guó)家的中國(guó)來(lái)說(shuō)�,擺在眼前的一個(gè)關(guān)鍵的問(wèn)題就是�����,“要讓所有群體能從經(jīng)濟(jì)增長(zhǎng)中分一杯羹”��。在這個(gè)問(wèn)題上�,公開(kāi)個(gè)人所得稅數(shù)據(jù)�����,讓信息更透明將不失為良策之一�。一個(gè)人盡皆知的真理是:“不要體溫計(jì)是不會(huì)讓發(fā)熱的人降溫的。”
在著作的第四部分�����,皮凱蒂并沒(méi)有逃避去對(duì)公共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議,他既對(duì)全球累進(jìn)制資本稅做出了思考����,同時(shí)堅(jiān)信“在相當(dāng)長(zhǎng)一段時(shí)間內(nèi),推動(dòng)更進(jìn)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都是知識(shí)和技能的擴(kuò)散”�����。雖然這種做法為他招致了很多非議——有多少人愛(ài)這部著作�,就有多少人恨它——但對(duì)不同意見(jiàn)的歡迎與接納恰恰是皮凱蒂在每次演講中都開(kāi)誠(chéng)布公的,“比起讓你們接受我的意見(jiàn)�,我更愿意你們?cè)谛闹袑?xiě)出屬于自己的第四部分。”
讓所有群體能從經(jīng)濟(jì)增長(zhǎng)中獲益
問(wèn)=徐見(jiàn)微 朱天元
答=托馬斯·皮凱蒂(Thomas Piketty)
問(wèn):你為何將這本書(shū)命名為《21世紀(jì)資本論》���?這個(gè)題目難免會(huì)使人聯(lián)想到卡爾·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��。
答:很多沒(méi)有閱讀過(guò)這本書(shū)(《21世紀(jì)資本論》)的人都會(huì)懷疑我是個(gè)馬克思主義者����,但事實(shí)并非如此����。我相信私有財(cái)產(chǎn),我所譴責(zé)的也并非不平等和資本主義本身,相比較而言�����,我更看重要建立一個(gè)公正的社會(huì)秩序需要怎樣的制度和政策���。
確實(shí)有很多人會(huì)拿這本書(shū)與《資本論》比較�����,但馬克思的觀點(diǎn)是��,資本利率趨向于無(wú)限下降�,最終導(dǎo)致資本收益率趨近于零��,從而引發(fā)無(wú)產(chǎn)階級(jí)革命�,我的結(jié)論則不如所暗示的那樣。我認(rèn)為財(cái)富分化不是永恒的�����,只是未來(lái)幾種財(cái)富分配方向可能性中的一種���。而資本收益率將永遠(yuǎn)大于經(jīng)濟(jì)增長(zhǎng)率,不平等的程度也是可以下降的。
另外一個(gè)明顯的不同是��,《資本論》更多集中在理論層面�,是對(duì)未來(lái)做各種估測(cè),它的背景是工業(yè)革命時(shí)代的歐洲�����,1860年左右英法等國(guó)的工資停滯不前����,企業(yè)的利潤(rùn)增長(zhǎng)則越來(lái)越快,馬克思生活在這樣一個(gè)時(shí)代背景下�����,理解時(shí)代所處的社會(huì)環(huán)境�,但這一時(shí)期的很多理論和著作缺乏大量的數(shù)據(jù)作為支持;21世紀(jì)的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們則不斷收集歷史數(shù)據(jù)����,建立越來(lái)越復(fù)雜的數(shù)學(xué)模型,但他們卻又忽略了我們所在的社會(huì)環(huán)境和歷史背景����。馬克思的出發(fā)點(diǎn)很重要��,但沒(méi)有多想廢除了私人財(cái)產(chǎn)以后的結(jié)果會(huì)怎么樣����。今天����,私人財(cái)產(chǎn)變得嚴(yán)重不平等,但可以設(shè)計(jì)行之有效的辦法�����,還是有很多的機(jī)制是可以在平等性問(wèn)題上產(chǎn)生作用�����,給我們的平等性帶來(lái)不同的動(dòng)態(tài)發(fā)展的��。比如依賴(lài)于公共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和稅收制度�,設(shè)立全球累進(jìn)資本稅。
最后一點(diǎn)���,自20世紀(jì)70年代起�����,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已經(jīng)對(duì)財(cái)富分配和社會(huì)階級(jí)問(wèn)題喪失了絕大部分興趣��,我選擇這個(gè)書(shū)名是想重新把分配問(wèn)題納入到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的核心���。這應(yīng)該是最核心的問(wèn)題,我們長(zhǎng)遠(yuǎn)怎樣發(fā)展�����,我們沒(méi)有任何理由認(rèn)為增長(zhǎng)時(shí)每個(gè)群體分配得到的收益比例應(yīng)該固化��。分配問(wèn)題要重新納入到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的核心�����,這離不開(kāi)對(duì)數(shù)據(jù)的分析和對(duì)歷史表現(xiàn)的分析�。
問(wèn):你剛剛提到你所譴責(zé)的并非不平等和資本主義本身,書(shū)中也提及真正讓人無(wú)法接受的是不平等超出限度����,那么有哪些跡象可以作為指標(biāo)表明這個(gè)限度已經(jīng)被超出?
答: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壞事�,關(guān)鍵問(wèn)題是判斷它是否正當(dāng),是否有存在的理由?����,F(xiàn)實(shí)中,有些不平等是有利于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的����,但過(guò)了度就會(huì)反過(guò)來(lái)危害經(jīng)濟(jì),我關(guān)注的不僅僅是不平等的水平本身�����,也會(huì)更大程度上關(guān)注不平等的結(jié)構(gòu)�����,即社會(huì)群體間收入和財(cái)富差距的來(lái)源�����,以及用以保護(hù)或譴責(zé)那些差距的各種經(jīng)濟(jì)�����、社會(huì)��、道德和政治評(píng)判體系��。
但在這個(gè)問(wèn)題上,并沒(méi)有一個(gè)數(shù)學(xué)公式可以用來(lái)證明不平等的水平太高或太低���,我們還是要根據(jù)歷史上的經(jīng)驗(yàn)來(lái)做出自己的判斷。歷史已經(jīng)給了我們一些教訓(xùn)���,雖然未必充分�����,但足以證明不能夠?yàn)榱私?jīng)濟(jì)增長(zhǎng)而制造極端的不平等���。
一個(gè)多世紀(jì)之前的歐洲,90%的社會(huì)財(cái)富屬于最上層10%的人群����,這樣的財(cái)富分配不僅不利于經(jīng)濟(jì)的增長(zhǎng),還造成了社會(huì)的緊張�����,在這樣的社會(huì)當(dāng)中基本是不存在中產(chǎn)階級(jí)的��。我們今天絕對(duì)不能夠再回到那樣一種極端不平等的情況���。
今天的美國(guó)����,10%的頂層人群占有70%左右的社會(huì)財(cái)富,雖然比例仍然相當(dāng)高��,但較19世紀(jì)的歐洲還是有了顯著的進(jìn)步����,絕大多數(shù)人可以擁有諸如一間公寓、一輛車(chē)子這樣的資產(chǎn)��。當(dāng)然很多人還是認(rèn)為美國(guó)的不平等現(xiàn)象嚴(yán)重����,所以需要有政治上的途徑,比如說(shuō)占首富10%左右的一些人多做貢獻(xiàn)�����。我不知道這是否可以作為答案���,但這個(gè)問(wèn)題是無(wú)法以一個(gè)簡(jiǎn)單的標(biāo)準(zhǔn)進(jìn)行衡量的���。每個(gè)人都可以拿出自己的觀點(diǎn)��。
問(wèn):那么如果為了經(jīng)濟(jì)的增長(zhǎng)而造成極端的不平等將會(huì)造成怎樣的后果���?
答:我沒(méi)有辦法對(duì)未來(lái)做出預(yù)測(cè),因?yàn)橛绊懙轿磥?lái)發(fā)展趨勢(shì)的因素非常多��。我書(shū)中提到了很多相互交織的因素����,馬克思認(rèn)為不平等會(huì)越來(lái)越大���,庫(kù)茲涅茨認(rèn)為不管哪個(gè)發(fā)展階段���,不平等還會(huì)繼續(xù)下降。其實(shí)沒(méi)有什么經(jīng)濟(jì)的宿命論�,完全取決于我們用什么樣的政策來(lái)管理經(jīng)濟(jì),從現(xiàn)實(shí)上來(lái)講���,美國(guó)不平等問(wèn)題增長(zhǎng)得最快�。
今天���,以中國(guó)為代表的新興國(guó)家的崛起��,某種程度上減少了收入分配的不平衡�����,但中國(guó)最富裕的階層距離中產(chǎn)階層的差距正變得越來(lái)越大�,這是相當(dāng)復(fù)雜的一個(gè)問(wèn)題。
今天的中國(guó)經(jīng)濟(jì)取得了巨大的增長(zhǎng)���,同時(shí)也該有更大的公平性�����。因?yàn)闃O端的不平等會(huì)危害社會(huì)的流動(dòng)性�����,伴隨著巨大的����、長(zhǎng)期的不平等�,就會(huì)造成教育資源的不平等,那么精英階層的孩子就會(huì)永遠(yuǎn)比其他人的孩子更容易獲得最好的教育資源���,從而獲取到最大的財(cái)富�。如果社會(huì)階層的流動(dòng)出現(xiàn)固化,就會(huì)對(duì)這個(gè)國(guó)家和社會(huì)構(gòu)成挑戰(zhàn)����,中國(guó)在新時(shí)期面臨的挑戰(zhàn)和改革開(kāi)放之初是絕不一樣的。
我們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不平等�����,那么我們今天是否有可能回到19世紀(jì)的歐洲那種情況呢�����?所有政策��、法律�����、社會(huì)的變化都可能改變結(jié)局����,既然我們不想倒退回去���,那么我認(rèn)為可以設(shè)計(jì)一些公共制度和政策來(lái)減少負(fù)面影響���,不僅僅是全球累進(jìn)資本稅����,還有其他途徑可以對(duì)公共財(cái)產(chǎn)進(jìn)行分配�,增強(qiáng)收入和財(cái)產(chǎn)的透明度,從而因地制宜地修改政策�����,同時(shí)還可以普及教育����,加大教育資源投入,因?yàn)樵谙喈?dāng)長(zhǎng)一段時(shí)間內(nèi)����,推動(dòng)更進(jìn)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都是知識(shí)和技能的擴(kuò)散。
問(wèn):雖然知識(shí)和技能可以成為晉升中產(chǎn)階級(jí)的通道�,但教育資源的平等本身就很難實(shí)現(xiàn),經(jīng)濟(jì)不平等造成的其他優(yōu)勢(shì)����,比如開(kāi)闊的眼界等等也會(huì)造成日后社會(huì)競(jìng)爭(zhēng)中的顯著差距���。
答:是的,沒(méi)有任何一種解決方式是完美的����,公正合理的考試制度也并不能保證對(duì)所有人公平,我所身處的法國(guó)雖然有很多考試�����,但也不能讓教育系統(tǒng)完全公正���。
以美國(guó)為例��,美國(guó)有著非常多的優(yōu)秀大學(xué)����,作為世界名校的哈佛大學(xué)����,調(diào)查研究發(fā)現(xiàn)哈佛大學(xué)學(xué)生父母的平均收入水平與美國(guó)家庭收入排名前2%的家庭水平相當(dāng)�,這暗示著美國(guó)較低的社會(huì)流動(dòng)性以及教育資源的不均衡。
在最近的15年間�,美國(guó)50%的人口受教育人數(shù)幾乎沒(méi)有增加����,而最富裕的25%的人口中��,絕大多數(shù)都接受了高等教育���,在以前����,這個(gè)比例還只占到一半��。所以說(shuō)每個(gè)國(guó)家在教育上的政策和投入的變化都可能影響貧富分化的走向���。
但我們的目標(biāo)并不是非常完善的���、平等的系統(tǒng),而是盡可能多的給底層家庭的孩子機(jī)會(huì)�����,讓他們向上走的通道不被封死����。將社會(huì)累積的財(cái)富重新投入到教育與基礎(chǔ)設(shè)施的建設(shè)�,這不僅是為了平等�,還為了我們生活在一個(gè)更有尊嚴(yán)的環(huán)境之中。教育可以提升人們的勞動(dòng)效率����,我們要在國(guó)家內(nèi)部降低不平等性,就要有非常強(qiáng)大的包容性的教育機(jī)制使得大家能有機(jī)會(huì)獲得更多的技能�����。
問(wèn):如果要加大教育投入��,就需要稅收作為保障����,同時(shí)你給不平等開(kāi)出的另一個(gè)藥方就是全球累進(jìn)制資本稅,但顯然這實(shí)行起來(lái)困難重重���。
答:如果要讓所有人得到高質(zhì)量的教育�,就需要有足夠多的稅收來(lái)支付整個(gè)教育支出���。歐洲有28個(gè)國(guó)家,多數(shù)稅收占到GDP的20%以上���,瑞典����、丹麥這樣的富裕國(guó)家則更高,他們有這么多稅收�����,怎么用�?相當(dāng)一部分用于投資與教育。像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這些沒(méi)有那么富裕的國(guó)家�,拿有限的稅收怎么用?用于高質(zhì)量的教育�、醫(yī)療、社會(huì)服務(wù)就對(duì)了����。在法國(guó),我們的公共支出沒(méi)有丹麥����、瑞典那樣高效率,所以應(yīng)該向他們學(xué)習(xí)�。而在中國(guó),由于教育體系的問(wèn)題��,家庭仍然需要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教育。稅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�����,取決于你怎樣使用它����。
當(dāng)然富人恐怕并不對(duì)多繳稅樂(lè)見(jiàn)其成,我之前和比爾·蓋茨聊過(guò)這個(gè)話題����,他對(duì)我說(shuō),我喜歡你的書(shū)���,但我并不想多付稅���。
問(wèn):那么從另一個(gè)角度來(lái)講,你認(rèn)為對(duì)富人征稅過(guò)多是否會(huì)影響一部分人工作和創(chuàng)造的積極性�����?
答:假如對(duì)所有人都征收80%的所得稅��,恐怕就沒(méi)有人去工作了,這是非常不好的��,也沒(méi)有人這樣去做��。高稅率必然只適用于高收入的少數(shù)群體�����,適用于當(dāng)貧富差距很大時(shí)那些占有多數(shù)財(cái)富的少數(shù)人�����。就工作積極性而言����,當(dāng)財(cái)富累積到一定程度����,更多的財(cái)富本身其實(shí)已經(jīng)不是積極性的最大來(lái)源了。比如說(shuō)比爾·蓋茨���,即使他不知道微軟可以創(chuàng)造那樣巨額的財(cái)富��,他也一樣會(huì)去發(fā)明windows�����。還有一點(diǎn)是����,雖然現(xiàn)在大公司給高級(jí)經(jīng)理人提供天價(jià)報(bào)酬,但他們?yōu)楣緞?chuàng)造的價(jià)值還是常常與這種收入并不對(duì)等�,很少證據(jù)表明,他們的管理給企業(yè)帶來(lái)了足夠多的額外價(jià)值�。
問(wèn):累進(jìn)制資本稅可以抵消一部分不平等,你在書(shū)中談到要將稅收用于加強(qiáng)福利國(guó)家的建設(shè)����,但現(xiàn)實(shí)中也有很多國(guó)家過(guò)度福利從而導(dǎo)致社會(huì)活力下降的例子,你認(rèn)為應(yīng)該如何把握好這個(gè)度��,從而避免走向過(guò)度福利社會(huì)���?
答:我們可以了解到���,不同的發(fā)達(dá)國(guó)家,他們的稅收對(duì)于GDP的貢獻(xiàn)度是不一樣的��,從30%到50%不等�����。比如說(shuō)美國(guó),30%左右����,相對(duì)較少���,他們就必須更加行之有效地去利用公共支出�����。瑞典稅收占GDP的比例可以達(dá)到百分之四五十�,超過(guò)40%�����、50%的水平是極少的情況����。
我們今天說(shuō)高福利國(guó)家有其弊端,像是老齡化的一些問(wèn)題���,所有人60歲就退休未必是好事�����,社會(huì)上的很多職業(yè)是完全可以工作到60歲以后的�����,根據(jù)現(xiàn)有的養(yǎng)老體系���,考慮到工作條件���,整個(gè)社會(huì)在這方面的負(fù)擔(dān)不要增加太多,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很大了����。
問(wèn):你怎么看待反腐作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之一?
答:腐敗可以說(shuō)是造成了最不合情理的一種財(cái)富不平等���,讓巨額財(cái)富源源不斷地流入極少數(shù)人手中����。所以把反腐作為當(dāng)前要?jiǎng)?wù)是完全必要的����。不過(guò)�����,若以為腐敗是導(dǎo)致極為不公的財(cái)富不平等和財(cái)富集中的唯一根源��,又過(guò)于簡(jiǎn)單�����。
進(jìn)行反腐斗爭(zhēng)讓幾個(gè)人坐牢還是不夠的�����。俄羅斯其實(shí)一直是這么做的,寡頭政治家控制金融�,讓一部分的財(cái)閥富裕起來(lái),做的不好了就抓起來(lái)送進(jìn)監(jiān)獄��,但我覺(jué)得這并不是調(diào)節(jié)不平等最好的辦法�,最起碼不是唯一的辦法。從實(shí)踐意義上來(lái)講�,必須建立一整套公共機(jī)制,使資本服務(wù)于整體利益�,包括在各個(gè)行業(yè)中發(fā)展各種新型資產(chǎn)和新型的參與性治理,還包括對(duì)收入和資產(chǎn)實(shí)行累進(jìn)稅制�。累進(jìn)稅制的理想形式是對(duì)所有收入和資產(chǎn)征稅�����,收入和資產(chǎn)水平越高��,稅率就越高��。
問(wèn):你對(duì)中國(guó)的貧富差距情況有過(guò)估算嗎��?
答:家庭經(jīng)濟(jì)調(diào)查初步的數(shù)據(jù)給我的印象是����,中國(guó)最近十五年不平等現(xiàn)象逐漸上升����,達(dá)到了與歐盟差不多的水準(zhǔn),甚至接近美國(guó)�����,但這種初步印象沒(méi)辦法得到數(shù)據(jù)的支撐����,對(duì)中國(guó)的情況,我缺乏充分的歷史數(shù)據(jù)���,還需要更多地觀察和分析中國(guó)以往的經(jīng)濟(jì)表現(xiàn)�����。相對(duì)于其他國(guó)家�����,中國(guó)最大的問(wèn)題是我很難獲得準(zhǔn)確的個(gè)人所得稅數(shù)據(jù)�����。因此我無(wú)法知道比如總資產(chǎn)100萬(wàn)-200萬(wàn)美元的人每年財(cái)富收入的變化����,或者總資產(chǎn)300-500萬(wàn)美元的社會(huì)階層的所得稅變化��,這些都是很關(guān)鍵的數(shù)字���。
現(xiàn)階段我們無(wú)法把中國(guó)的所得稅數(shù)字與其他國(guó)家進(jìn)行比較�����,中國(guó)在金融透明度上做得還不夠�,中國(guó)最近的財(cái)富和資本收入比前幾年有所上升,這和房?jī)r(jià)的走高息息相關(guān)����,另外一點(diǎn)與其他國(guó)家不同的是,中國(guó)的公共資本在國(guó)民總財(cái)富中的占比達(dá)到30-40%����。綜合這些因素,很難估算中國(guó)收入差距的演變���,一個(gè)國(guó)家個(gè)人所得稅的數(shù)據(jù)應(yīng)該真正服務(wù)于人們���,數(shù)據(jù)公開(kāi)是最好的方式。這將可以����,至少應(yīng)該和反腐敗相互作用,基于抽樣調(diào)查和自主申報(bào)而得出的官方數(shù)據(jù)往往會(huì)低估財(cái)富不平等的水平�����,只有強(qiáng)制性的稅收數(shù)據(jù)才能得出更為準(zhǔn)確的結(jié)果���,最近����,中國(guó)正準(zhǔn)備公布一些公共資產(chǎn)的報(bào)表,這是以前沒(méi)有的��。要知道�,不要體溫計(jì)并不能讓發(fā)熱的人降溫,中國(guó)現(xiàn)在更需要透明度�,如果能對(duì)遺產(chǎn)和財(cái)富進(jìn)行累進(jìn)式的稅收制度,就可以讓所有的群體從經(jīng)濟(jì)增長(zhǎng)當(dāng)中分一杯羹�����。這一點(diǎn)對(duì)中國(guó)在未來(lái)進(jìn)一步的發(fā)展非常重要��。
問(wèn):你在本書(shū)的第四部分給出了緩解貧富差距在政策方面的經(jīng)驗(yàn)教訓(xùn)����,同時(shí)又在演講中多次強(qiáng)調(diào),你并不介意讀者與你的意見(jiàn)相左���,這是為什么?
答:我遇到過(guò)許多問(wèn)題�,很多人都把我當(dāng)做一個(gè)現(xiàn)實(shí)問(wèn)題的解決者,希望我在提出問(wèn)題的同時(shí)���,能給予現(xiàn)實(shí)立竿見(jiàn)影的改變�����。這并不是我的初衷���,我在寫(xiě)作的過(guò)程中���,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和數(shù)據(jù)是為了展示我們這個(gè)世界所面臨的現(xiàn)實(shí)。崇尚自由競(jìng)爭(zhēng)的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��,如何變成了只為高層和少數(shù)人服務(wù)���,又是如何促進(jìn)了新的不平等�����。我只想解釋這樣一種現(xiàn)實(shí)����,讓更多的人意識(shí)到我們現(xiàn)在所處的困境����。在不同的國(guó)家中�����,不同的困境有著不同的形成原因��,無(wú)論是在歐洲��、日本��、美國(guó)或者是在中國(guó)�����,有的是因?yàn)槿狈τ行У氖袌?chǎng)監(jiān)管�����,有的是因?yàn)闄?quán)力的濫用與尋租���,有的是政府的責(zé)任,我無(wú)法給出統(tǒng)一的答案與結(jié)論��。這需要全球資本市場(chǎng)的透明和政府行政的高效與廉潔����,這是無(wú)法一勞永逸地解決的。
我覺(jué)得有些人對(duì)我最大的誤解在于�,認(rèn)為我是一個(gè)大政府的提倡者或者是對(duì)于自由經(jīng)濟(jì)的批判者,這些往往來(lái)自于偏見(jiàn)和誤解�。冷戰(zhàn)結(jié)束以后,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界對(duì)于自由市場(chǎng)與資本的信奉達(dá)到了無(wú)以復(fù)加的地步��,這也使得許多人從中受益����,但是滋長(zhǎng)了新的不平等與壟斷,資本的收入率夸張地高于產(chǎn)出率�,這是整個(gè)資本市場(chǎng)的病態(tài)。我們需要的是調(diào)整與反思���,讓資本的效益可以流動(dòng)到每一個(gè)參與者身上�,而不是讓大財(cái)團(tuán)和他們的繼承者獨(dú)吞��。累積的財(cái)富應(yīng)當(dāng)以更有效的方式回流于市場(chǎng)或者進(jìn)行有效的公共建設(shè)�,許多國(guó)家都在進(jìn)行這一方面的調(diào)整與改變,我樂(lè)于見(jiàn)到這一點(diǎn)��。因此我并不是別人所認(rèn)為的是一個(gè)現(xiàn)有經(jīng)濟(jì)秩序與分配政策的挑戰(zhàn)者���,我只是反對(duì)新的并正在不斷加劇的不平等�,不管這是來(lái)自于財(cái)富還是特權(quán)。